韩国电影也不行了
“我又被威尼斯电影节和朴赞郁欺骗了,没有笑点,没有快乐,只有失望。”
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数据,截至9月30日,由朴赞郁执导,李秉宪、孙艺珍主演的《无可奈何》共计在韩本土累计观影人数超过115万,连续6天占据票房冠军。
然而,仅6天赏味新鲜期过,迎来的则是吐槽大于夸赞的口碑持续走低以及单日观影人次的走低。根据韩国最大门户网站Naver的评分显示,评分在开画后持续下降、维持在6分左右浮动,远远低于朴赞郁2022年上映的8.98分作品《分手的决心》。

事实上,一度被看作是得奖领跑者、金狮奖热门、影后热门的《无可奈何》,甚至被视为有望借助海外声誉反哺国内票房的救命稻草。但最终却零封收官,继续维持着今年韩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陪跑纪录。
整体上看,今年全球电影业均面临一定的低迷期,而韩国电影业则率先一步暴露出更为严峻的形势。
韩国电影也不行了?
作为人口不过5000万、却是全球十大票仓之一的韩国,其电影产业在今年正面临着数十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最近,韩国文化部记者会提到,“电影行业需要CPR级别的紧急措施,如果没有紧急干预,生态系统可能会在几年内崩溃”。这一发言并非危言耸听。
截至今年7月,韩国电影院上座率仅为5000万张票,这也是2004年以来(不包括疫情年)最低的一次。尤其是本该为票房旺季的春节档前后,包括宋慧乔主演《黑修女们》、权相佑主演《漫画威龙2》、奉俊昊导演好莱坞大片《编号17》等具有强号召力的演员、IP作品,都未能掀起观影热潮,甚至不乏达到将将回本后,火速上线流媒体平台。同样的,被寄予厚望的暑期档,也因李敏镐与安孝燮主演,且是大热IP改编的《全知读者视角》口碑扑街,难以挽回观影人群,票房等市场核心指标继续下滑。

与此同时,韩国电影的产量、投资规模、财团制作预算等方面也在持续降低。
一方面,自2021年以来,韩国电影实际上消耗的是前两年推迟发布的电影储备,而今这些存货也已经走向枯竭。另一方面,根据韩媒报道,今年电影制作预算超过30亿韩元的电影也在骤降,CJ E&M、乐天、Showbox、NEW、Plus M五大商业电影发行商的投资规模大幅缩小。
这些长期主导市场的头部公司收紧,也是韩国电影行业困境的直观体现。乐天文化工作室内容业务负责人Lee Kyung jae就曾对韩媒表示,“所有投资人、分销商都在挣扎,几乎没有任何一部电影的制作开了绿灯”。
毕竟,在2019年以前,这些头部发行商能够做到一年供应超40部电影,今年却共计不到20部。即便是名导如李沧东,其汇聚薛景求、赵寅成、全度妍等忠武路头部演员的新作《可能的爱情》,如今也因难拉到投资搁置;像CJ E&M今年仅投资发行了朴赞郁导演《无可奈何》、李相槿导演《恶魔搬进来了》。
据悉,《无可奈何》为配合韩国文化部门提高电影上座率的特别举措,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同时也开启了本土预售。截至当下,根据韩国电影委员会的数据,预售仅达到29%(约10万张票)。这一数据也十分惨烈,与春节档后期重映的台湾地区经典作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旗鼓相当”。

不仅仅是在本土,今年在国际影坛方面,韩国电影也同样面临韩媒所称的“屈辱”处境。
洪尚秀、奉俊昊、朴赞郁等大导新作在柏林、戛纳以及威尼斯等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均出现零入围或零获奖。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极为罕见的惨淡面貌,更是韩国电影首次出现未能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窘况。
此外,部分韩媒也指出,由于今年8月朴赞郁因“工贼”事件被美国编剧工会开除,也间接影响了韩国电影创作者在全球电影行业的待遇,不乏出现韩影在颁奖季被隐形冷待的可能性。
当然,从全球来看,不仅韩国,包括票仓大头美国、中国等电影市场都进入了相对的低谷期,比如美国市场超级IP失灵导致票房下滑、日本与中国内地市场真人电影边缘化明显、依靠“多年磨一剑”的动画电影续命。
而跌落神坛的韩国电影,只不过率先走到了崩溃临界点。
韩国电影如何自救?
韩国电影如今的处境,有一定作茧自缚意味。
如上文所说,清空存货是这几年韩国电影市场最主要的产出模式,但受制于题材、时代等多重因素影响,能否盈利的不确定性更大。根据韩国电影委员会数据,去年共计发行37部商业电影,只有10部收回成本。这也直接导致投资者更加谨慎,在有限的投资内,低预算、低质量、低产量的螺旋式下降,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恶化。
再加上,2023年,韩国323部电影被曝出夸大票房收入、伪造达267万张票,电影院、发行商等业内共计69名造假犯参与其中。这一丑闻也导致多位导演、制作公司项目陷入投资困境,影响持续至今。

再者,受到OTT(Over The Top,流媒体)的冲击,人才被虹吸也间接影响着忠武路的活跃。尤其是Netflix入驻韩国市场后,加大线上网剧、网络电影的投入开发,不乏出现《鱿鱼游戏》这样精良班底、大IP、现象级作品的问世,也吸引了传统电影行业创作者“下凡”。
在高片酬、冲奖的诱惑下,影帝影后、名导名编开始扎根流媒体。比如部分高人气的忠武路演员片酬能够达到10亿韩元(约514万人民币)一集,而Netflix更是每年挖走13%的韩国电影创作人才(2023年公开数据)。近期,在网络电影《K-Pop猎魔女团》的现象级成功案例下,韩国电影的人才流向或也进一步向OTT迁移。

面对如此紧迫的现状,一方面,韩国政府也加码推出救济政策。9月5日,韩国文化部发布官方说明,表示明年将向电影业注入1.08亿美元,相比今年预算将增长80.8%。而这也是自2022年的疫情救济之后,规模更大的一次扶持投入。
为了进一步刺激本土观众走进电影院,韩国政府对于海外剧组赴韩宣传的“绿灯”近乎常亮,甚至不乏通过互访、交换综艺或线下活动等拍摄等形式。比如今年上半年,汤姆·克鲁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松重丰、斯嘉丽·约翰逊等均时隔多年罕见来韩,除了见面会外,还有与K-Pop爱豆联动、拍摄韩国旅行纪录片等方式宣传新作。

与此同时,除了借由釜山国际电影节之际扩办FLY计划(电影领袖孵化器)选拔新兴人才外,随着李在明的上台,此前被大规模缩减预算资金的首尔独立电影节(SIFF)也得以恢复。这也为创作者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电影行业创作者的人才的活跃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
此外,为了适应流媒体时代的大众观影习惯和影院高票价的问题,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与文化部联合推出发放优惠券计划,刺激观众区线下消费。像在9月初,共计发布188万张观影优惠券,每张票可减免6000韩元,最低能够达到仅需支出1000韩元便可观看一场电影。数据显示,这种降低消费门槛的举措也切实提高了大众重返影院的消费意愿,日均观影人次达到了43.5万,较之前增长1.8倍。

而自2019年以后,韩国影院不断加码的老片重映策略,也在当下被看作是韩国影院的“生命线”。据韩媒统计,仅在去年就有228部旧作重映,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今年规模则进一步扩大,比如今年号称史上最长版《霸王别姬》的重映、《少年的你》《不能说的秘密》等华语经典作也成为救市热门等。
不仅如此,还有如连锁影院运营商Megabox这般,通过拿下艺人演唱会纪录片/大电影、《狼人》《不绅士战争部》等独家播放权来打出差异化。不过,这种屏幕垄断的做法也同样引发电影行业抗议,认为无法保证观众的可访问性,即难以让新作品、新电影人的成长被观众关注。
此外,影院的变革也同样瞩目。像CJ CGV、乐天电影院、Megabox等头部影院品牌均推出“电影+”的联动营销活动,如Megabox便推出了边做手工边看电影的观影方式,以及“在影院中小憩”的非常规定向营销活动,即上班族、学生仅需要花费1000韩元,便可在午餐时间享用两个小时影院躺椅的休息时间。

可以说,如今韩国电影业自上而下的多种路径尝试,虽有一定成效,但最终能否解决问题,仍然有待观察。想要打破冰冻状态,还是需要回归电影行业的初心——让电影成为电影。
结语
但回过头看,观众真的不爱韩影了吗?
本质上,韩国影视作品受到青睐,并非在于华丽特效亦或是神乎其神的视觉效果,而是以故事叙述取胜,这恰恰是韩影通行全球市场的优势所在。然而,自《寄生虫》成功冲奥后,韩国内容创作似乎陷入了大制作、豪华班底的执着怪圈。
在月初的海浪电影周,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也提到,“我们老学好莱坞,不过学歪了,就学到了浪费钱。咱们老跟好莱坞比,可人家是全球票房,我们只有单一市场,而且绝大多数收入来源只有票房”。
像投资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唐探1900》等大片的中影集团,其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净利润暴跌245%、亏损1.41亿元,原因便是在于主投、参投电影票房未达预期。而这同样是韩国电影所面临的大片效应失灵。
显而易见,如今的电影市场已然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承担创意风险、大片滑铁卢。
不少韩国影评人也认为,在投资冻结、人才缺失、观众流失的持续下,将影响未来的电影生态。近两年,随着韩国影视内容的制作含金量下降,Netflix对韩国内容创作的投资重心也有明显向日本迁移,甚至不乏将韩国演员、导演团队打包日剧市场合作的现象。
诚如目前韩国电影行业所持的悲观态度——“真正的危机始于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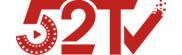









暂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