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依然经典,他可能是最会拍青春片的导演
1985年2月15日,导演约翰·休斯执导的《早餐俱乐部》正式上映。四十年过去后,你会发现它是青春电影史上鲜有的既成功捕捉到了一个时代的灵魂,又能轻松地穿越世代,与一代又一代成长于不同环境的年轻人进行持续对话的一部作品。
《早餐俱乐部》

在视觉特效突飞猛进的八十年代,《早餐俱乐部》颇为另类,不能更日常的校园场景与从始至终缺乏激烈冲突的情节,却细腻地捕捉到了拒绝被“标签化”的一代关于身份认同、归属感与人际关系的迷思。
约翰·休斯这封写给年轻人的真诚信函,在岁月的流逝中承载了远超创作之初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命题,在二十一世纪已过四分之一的当下仍具有值得玩味的现实意义。

击碎对青少年的刻板印象
五名青少年被迫在封闭的高中图书馆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周六,这种看似单调的设定却巧妙地将一个惩罚性的场所变成了“创伤疗愈互助会”的现场。
整整九个小时的留校惩罚,让原本互不相干甚至带有敌意与强烈偏见的青少年拥有了卸下伪装的机会,不仅是与他人间的隔阂,一同消解的还有那些阻碍青少年认识自我的内心屏障,实现了从对立到寻得共鸣的跨越。

约翰·休斯开场便用大卫·鲍伊的歌词与被击碎的玻璃宣告了其试图打破青少年刻板印象的意图,而更有趣的是他选择了最符合美式青少年刻板印象的五个人:
光鲜富有的“公主”克莱尔·斯坦迪什、活跃于校队的“运动员”安德鲁·克拉克、成绩优异的“书呆子”布莱恩·约翰逊、举止怪异的“怪咖”艾丽森·雷诺兹以及把“叛逆”两个大字写在脸上的“罪犯”约翰·本德。

约翰·本德
换做是《十三号星期五》这样的同时代砍杀片,这五名青少年简直是人们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受害者阵容,每个人的标签都必然会成为其死亡的诱因。
而约翰·休斯则用一整部电影系统地解构了这些人设,揭示了这些标签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都是饱受压力与心灵创伤折磨的普通青少年,他们都同样被父母的期待、同辈的压力和对未来的迷茫所困惑,他们还没有成熟或强大到可以独自处理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一切。

当他们最终走出学校的时候,你会发现本德起初令人生厌的暴躁言行只是掩饰原生家庭暴力与进行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安德鲁会为自己的霸凌行为深感羞耻,布莱恩会为了一次成绩的失误而想不开,克莱尔其实也清楚自己所谓的优越感需要费劲伪装,而艾丽森其实并不介意接纳全新的服饰风格,只是此前没有机会。
内心深处,每个人其实都渴望被理解,渴望不用付出代价的坦诚相待,也都有着害怕被伤害的脆弱部分。
谁也不知道片尾蹦出的火花究竟是会延续下去还是转瞬即逝,但至少在这个周六的尾声,五人相互之间的深刻共情是真实存在的,约翰·休斯用如此真挚的情感向每一位观众诉说着“和解”的可能性。

属于八十年代的时代印记
《早餐俱乐部》的故事虽然只停留在一座校园当中,但也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影片深刻地根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经历的剧烈转型。
在美国时任总统里根的领导下,美国社会从六七十年代的民权、反战运动等集体主义理想转向了以减税、放松管制、追求个人成功和物质财富为核心的“里根时代”。片中五名年轻人各自的困境正是这一时代价值观的直接产物。
安德鲁的压力来源于其父亲对于“赢家”和“肌肉力量”的推崇,其与里根时代盛行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大行其道的硬汉形象相关联,以史泰龙、施瓦辛格为代表的好莱坞硬汉将具有超强男性气质的保守主义英雄形象推到了顶峰。
而受其影响,安德鲁采用了简单粗暴的霸凌手段来试图弥补其与所谓主流男性形象间的差距,去迎合其假定的他人期待。

安德鲁·克拉克
布莱恩承受的学业压力则可被视为里根教育改革强调“提升学生成绩和教育质量”的直接体现。
可以说片中青少年的内心挣扎一部分便来源于从出生起就被灌输的“成就驱动”价值观,这也是约翰·休斯一贯在作品中试图去反叛的,如此刻画也使得“新鼠党”(Brat Pack)在银幕上定义了八十年代青少年面貌的同时,真实地呈现了一代青年面临的实际困境与挑战。

布莱恩·约翰逊
《早餐俱乐部》也简明扼要地点出了里根时代“郊区家庭”光鲜外表下出现功能失调的现实。电影所处的时代正是“一对已婚夫妇带着孩子在郊区拥有一栋独立住宅”的“美国梦”被当局广泛推崇的当口儿,而事实却是单亲家庭比例迅速上升,物欲至上的浪潮也冲击着传统的家庭结构,导致家庭内部的情感疏离。
在外界看来克莱尔一家的生活富裕美满,然而实际上恶劣的父母关系直接使克莱尔沦为一枚“棋子”,父亲只会用金钱去补偿女儿情感上的缺失。艾丽森则是彻彻底底遭到了家庭的情感忽视,而本德则身处更糟糕的暴力家庭当中。

克莱尔·斯坦迪什
八十年代同样是美国代际冲突极为激烈的一个时期,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已然步入中年,不再充当反主流文化的摇旗手,反倒寄希望于保守主义政客倡导的传统观念,于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新一代的分歧不断加大。反映到片中便是以弗农为代表的成人权威与五位青少年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弗农是一个典型的被体制化、被现实消磨掉棱角、内心早已麻木的成年人,恰如清洁工卡尔的当面吐槽:“那些孩子没有变,是你变了……若你是16岁,你对你自己会有什么想法?”

弗农
约翰·休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八十年代代际冲突的本质,即所谓的权威与主流缺乏共情能力与同理心,暂且拥有主导能力的他们被傲慢蒙蔽了双眼,不愿承认正在用叛逆冲击社会规训的年轻人必将改变世界的事实,只是一味地用“世风日下”维护自己狭隘的认知。
约翰·休斯也并未将一个世代一棍子打死,与弗农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洁工卡尔能够一眼看穿青少年们的心思,对弗农的傲慢也毫不嘴下留情,作为一个“有心”的成年人,卡尔代表了代际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清洁工卡尔
除却对世代的精准剖析,《早餐俱乐部》本身在视听方面也成为了后世对八十年代进行幻想的范本。
服装设计师玛丽琳·万斯在片中巧妙勾勒出了八十年代青少年亚文化的图景,本德通过纹格衬衫、牛仔外套、无指手套等服装所展现出的叛逆与不羁成为了不少年轻设计师“梦开始的地方”。
Simple Minds乐队为本片演唱的片尾曲Don't You (Forget About Me)更是成为了一众青少年心中的“圣歌”,歌中的“嘿!嘿!嘿!嘿!”与本德挥向空中的那一拳无疑是主角们对那个不理解他们的世界声嘶力竭的呐喊,在青少年心中引发着强烈的共鸣。

约翰·休斯眼中的青春期
约翰·休斯不仅能够捕捉到青少年心中略显稚嫩而又难以捉摸的特质,还凭借《十六支蜡烛》《早餐俱乐部》《春天不是读书天》等一连串青春佳作彻底改变了这一题材的面貌。

《春天不是读书天》
将“青少年”视为一个独立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文学”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已出现在美国社会,但这一概念被普罗大众逐步接受则始于战后的五十年代,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与新的娱乐消费、历史共同记忆等因素放大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也加速了这一年龄类别的青少年在文化上的自我塑形。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诸如詹姆斯·迪恩主演的《无因的反叛》、马龙·白兰度主演的《飞车党》等青少年剧情片才首度登上大银幕。

《无因的反叛》
到了七十年代,青少年题材开始与恐怖片、音乐剧等传统类型片融合,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厌蠢症游乐场”的美式青少年砍杀片,大肆剥削着对青少年群体既有的刻板印象。
直到约翰·休斯出现,专注于青少年群体本身的电影才开始成型,约翰·休斯眼中的“青春期”迅速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风格在浮夸的流行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约翰·休斯不断变换着故事的视角,性格截然不同的主人公们却又都得到了创作者给予的尊重,在平凡的故事中得到了异常丰满的人物塑造。
恰如美媒MovieWeb给出的评价:“约翰·休斯彻底改变了好莱坞和公众对青少年以及美国青年的看法。”

约翰·休斯
讽刺的是,四十年过后,现如今的社会似乎比过去更需要约翰·休斯的视角。
社交媒体的泛滥以无处不在的触角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然而却并未真正地通过拉近距离来撕下种种标签,在信息爆炸环境下的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虑、抑郁,在迅速流失注意力的同时也将定义自我的能力让位给了他人的审视。
充满着刻意迎合的人设只为博得所谓的流量,身居幕后的算法重新用“标签化”引导了新一代审视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向你灌输着“总要加上几个tag”的想法,这一切都与《早餐俱乐部》中倡导的坦诚背道而驰。

电影中叛逆的一代似乎绝大多数最终也未能避免走上被规训的老路,现实给了片中“我们长大后会变成我们的父母吗?”的疑问一个略显悲伤的答案。
对《早餐俱乐部》的纪念绝非单纯的怀旧,也绝不仅仅是远远回望那一特定年代的精神风貌,而是回到那个再日常不过的星期六,在五位主人公的坦诚对话中思索自身的处世之道。
关于如何在新的时代中消除偏见以及建立健康的认同感,电影无法直接作出解答,但我相信每个人在重温之后都会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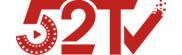









暂无数据